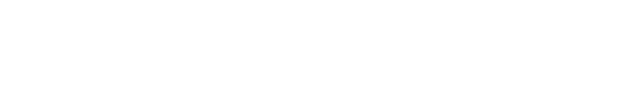3月8日,桑德尔再次来到上海,出现在华东师大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上。距离2010年3月19日在复旦做《什么是正义》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六年。那几天,仿佛哈佛大学最红火的网上课程《公正》搬到了复旦课堂。基于社群主义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而奠定了学术地位,桑德尔,这位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爱用讲故事方式深入伦理道德讨论。2010年之际,哈佛每6名本科生中就有一人注册过他的《公正》课程,他依据博士论文改编的学术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也被改编成各种通俗版本,如《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桑德尔成了当时的热词,大学生知道关于火车司机选择压死一位亲人还是五位路人,救生船上仅存的四人为了存活是否该生吃奄奄一息的男孩,这样的桑德尔式道德困境故事,就好像今天的学子应该知道引力波,国人应该知道屠呦呦获得诺奖一样。
又一个三月,桑德尔来了,这一次,并没有公开演讲,三天的国际研讨会,也没有安排主题演讲。但是,和他一起来的,是一群实力派的国内外哲人:杜维明、安乐哲、陈来、杨国荣、黄勇、万俊人等等。活动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哲学系、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办,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会长、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杨国荣具体发起和组织了此次讨论。地点就在2014年曾举办过为期一周的“李泽厚学术研讨会”的理科大楼508室。
学习还是互鉴: 不同于12年前的 “罗蒂与中国哲学”研讨会
19世纪末,黑格尔曾质疑过:中国是否有哲学,从而引发了几代中国哲人的“正名”努力;然而,进入20世纪,几乎伟大的哲学家都来过中国,上个世纪有罗素、杜威、萨特,这个世纪更有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泰勒等。在开幕致辞中,杨国荣提起了12年前的华东师大主办的“罗蒂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尽管罗蒂关注广义的文化,桑德尔更聚焦伦理和政治议题,但是,他们的著作同样都在中国受到关注,其思想也广为传播。而桑德尔所关注的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家们多年来的问题意识的出发点,比如:道德何以必要?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把握权利与善之间的关系?
杨国荣指出了世纪性的转变,西方哲学家同样也开始关注中国哲学,而并非只是中国学者渴望学习西方哲学。但是,同样的挑战放在当代中西哲人面前,如何打破只向自己的传统资源区挖掘的局限性?“今天,哲学的思考不能只局限在一种思想资源中,中西方同样需要关注多样的传统。”
带着这样的共识,昨天展开了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做了《精神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自我》的主旨发言,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聚焦《儒家伦理对“人”的构建:一个好的起点》,华东师大的青年教师德安博就“儒家伦理角色和社群回应的三个挑战”做了阐述,洛纽拉马利蒙特大学王蓉蓉做了《桑德尔正义社会的条件之一:参与不同道德观点否认公共讨论》的陈述;而杨国荣做了《正义再思考:其意义与限度》的主旨演讲。与往昔的研讨会不同的是,每一节主题发言后,都安排了充分的长达半小时的讨论,桑德尔在一节讨论中,直率地说:我需要尖锐的批评。不同语境下,不同的理解,在近四小时中,对话充分展开。
安乐哲问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超越世俗人文主义?
在杜维明主旨发言后,安乐哲提问,诞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的世俗人文主义如民主、文明、自由等具有500年的历史,但在处理当代政治生活中,也暴露了其一定局限性,如何看待“精神人文主义”和它的关系,是否要替代和覆盖。“精神人文主义”是杜维明近几年思考的一个核心思想,在下午接受记者的独家采访中,杜维明认为这是当代学人问题意识的切入点,并非简单的对儒家传统概念的延续。在讨论中,杜维明回应,精神人文主义不是要简单地替代世俗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并不因为世俗人文主义出现的极端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某些失败,就否认它是普世价值。其实早在1948年,中国人张彭春作为联合国《人权宪章》执委撰写文稿时,就用了儒家的“良知”概念将之转变为“良心”写进了宪章,丰富了人权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视野超越了西方的一神教理论。哈贝马斯长期研究世俗人文主义,但后20年有了宗教研究的转向。查尔斯·泰勒和德里达的思想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但同时,精神人文主义也不认为中国在探索的道路,只是中国特色,它也将是为人类探索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杜维明强调,精神人文主义包含天、地、群、己四个维度。
桑德尔问杜维明: 是否有第三种形态的“人”?
讨论的焦点也聚焦到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和“成人”。在回答“仁”的主体性时,杜维明认为仁是基础,它应该是每个人能自然能产生的。古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就是生动写照。桑德尔询问杜维明,按照他的两个分类,一种是作为天地一部分的人,另一部分是社会联结网中的过程中的人,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人,处于刺激状态中的人,即道德关系由我选择而产生的人?杜维明以“肉身成道”做了形象的解释,他认为人是具有超越性的。比如,父亲就有个成为父亲的过程,而在过程中,他不断接受着外界的刺激,不断有反应,最后,由于拥有内在力量,便能超越这个角色的局限性。
杨国荣回应桑德尔: 正义是否具有限度,可否超越?
杨国荣在主旨发言中就桑德尔的正义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社会的衍化看,正义本身具有历史性:以权利为关注的中心,使正义很难超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和程序层面的公正,从而也无法使人的存在意义得到充分的实现,后者决定了它将随着社会的演进而被超越。以社会资源或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为历史前提,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实现,具体地表现为人的自由发展,后者既以成就自我为内容,又以成就世界为指向。
讨论中,桑德尔质疑杨国荣所说的正义超越的可能性,并希望杨国荣从历史中,以具体的现象来说明这种可能。杨国荣以家庭为例,对此作了回应。杨国荣认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也存在资源的获得与分配的问题。然而,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家庭之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也主要不是以个体权利为依据,而是在更实质的层面基于不同成员的现实需要。蕴含于以上资源获取与分配模式之后的,是一种责任的原则或责任的观念。权利侧重于自我的资格和要求,相对于此,责任所指向的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切,而在资源的分配之中,这种责任和关切具体地便体现于对相关成员现实需要的注重。较之其他社会存在形态或单位,家庭对自身成员发展资源的安排,确乎更多地出于责任、基于需要,在这一社会结构及其运行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对基于权利的正义原则的某种超越。从实质的层面看,家庭确乎主要不是奠基于正义原则之上。以上事实同时也表明,在社会本身的演进中,走向以关注需要为中心的实质平等、真正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历史前提与内在的根据。
桑德尔之问的三人餐桌对话: 假如船上只有世界上最后4个男人
哲学的研讨会例来不乏先哲的被“在场”,上午三个多小时的讨论,黑格尔、亚里斯多德、孔子不时出场,康德、王阳明频频被搬来佐证,德里达、哈贝马斯也出来助阵。哲人们的晚餐也不例外,总有几道自制的“哲学玄思”来练脑,并让哲人们乐此不彼。从晚餐上传来这样的三人对话。
六年前,童世骏曾在复旦主场与万俊人点评桑德尔的《什么是正义》的演讲,桑德尔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五点点评,尤其是最后一点“道德选择有时未必来自理性,而是来自直觉。”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傍晚,有趣的对话延续着:
童世骏:假如那船上的四个人是全世界最后4个男人,他们是否就有正当理由想方设法活下去,哪怕把那个生病的男孩吃了?
桑德尔:仅仅有男人还不够啊,他们活下来,人类还是会消失的。
童世骏:假如世界上其他人都是女人,只有他们活下去,人类才有可能繁衍,他们是否应该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呢?
桑德尔:这倒使得问题有点复杂了。
童世骏:据说北京猿人是吃人的;假如我们不愿意他们那么野蛮,宁可他们不吃人而饿死,那就意味着后来就没有中国人那么道德的一个民族了。
杜维明:《孟子·公孙丑》里有一段话,有人问孟子,孔子与伯夷、伊尹在哪些方面是共同的,孟子回答说,孔子和他们都认为,哪怕只要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可以得到天下了,那也是不能做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童世骏:罗尔斯曾引用康德的话,“如果正义泯灭了,人类就没有理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句话听上去很好,但恐怕会被恐怖主义利用吧。他们会说,既然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他们眼中的正义,他就有权毁灭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关键是,对正义的理解是各有不同的。
桑德尔:那你是认可了相对主义的正义观,而不承认实在论的正义观了啰?
童世骏:那倒不是,我只是好奇。即使承认实在论的正义观,我们都要承认个人观点都有点暂时性质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根据我所认定的正义是否存在于世,就判断说人类是否值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太武断了?
也许,这只是一个放松的哲学家们之间的“脑筋急转弯”,但就像杜维明下午接受记者专访时所说,“假如停止工作,我会干什么?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他的生命不止,思想就不会停歇,无法分清思想应该在工作时还是休息时。”而三位哲人的不同身份,也让记者再次回想到研讨会一开始时,桑德尔对曾经的老师和同事、哈佛燕京学社13年社长的杜维明先生的一段话:多年来,杜先生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学习的(learning)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teaching)文明,这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