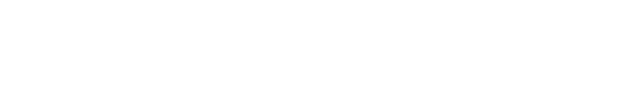近日,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彭国忠教授撰写的文章“《乐记》: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原发表于《文学遗产》2014年5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
以下为文章摘录:
《乐记》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官颁音乐典章,作为《礼记》的一部分,而成为儒家经书。宋代将《礼记》纳入科举考试的九经或五经中,从而使士人从少小时便接受了经文经义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其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发言立行,还是创作吟诵,都大体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行事,至少不违背其精神。
当宋人发表音乐见解和词学论述,品评词人词作,也就是进行所谓词学批评时,自会自觉地遵循《乐记》的思想,运用《乐记》的话语。《乐记》中的许多概念、语词,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表现,实已成为宋代词学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宋代词学批评,每以《乐记》为法,《乐记》实为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
音由物起,感物而兴:词乐批评
宋代的词乐批评,首先表现为遵从《乐记》音由心起、感物而生的精神,一是由此探索词之起源。
韩琦论雅乐,认为自物感之精神实质到文字,皆来自《乐记》,目的在于论证音乐非乐器使之然,乃是人心感于物使之然;而欲制作雅乐,必须创造治世的整体环境,使百姓自治世中感受到歆乐、和谐,从而感动内心的喜、悦、平、和之气,先古雅乐便可兴生。朱子虽然对时人不晓音乐器数不满,表现出与韩琦认识的不完全相同,但关于音乐起于人心的看法则一。
宋人对词之起源的探索,经由不同的路径,有从长短句句式入手的,有从词乐切入的。而通过词乐研究词的源头,宋人的观点也呈现出开放性。在唐宋词的比较中,沈括坚持哀乐情感是音乐(含词)的本源,“哀乐与声相谐会”,这便清楚地说明了词(乐)之起源。王灼继承《乐记》乐由心生等思想,而批评先乐后词的填词方式,认为应该是人心感物而有诗(歌词),有诗(歌词)之后而有声律,有声律而有乐歌。这反映出他对燕乐性质认识的一定混乱。
《乐记》固然只论乐,较少涉及配合燕乐歌唱的词,但这不是混淆“词”或“诗”与“音”或“乐”等概念,而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诗乐配合,文词与声调一致。
声与政通:词与社会、时代关系的表述
声与政通,考察的对象显然包含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三种类型。尽管有着治世、乱世可谓“世”,亡国不称世因其国将亡无复继世;以及治世、乱世皆云政,亡国因国将亡无复有政而称“其民困”之别,但人们往往并不如此细微区分而是整体考察。
声与政通观念,在宋人进行词学批评时,首先表现为直接阐述词关治体这个思想。宋人运用《乐记》“声与政通”思想于词学批评,最为成功的案例是指认一些词作反映了本朝政治之清明,风俗之淳厚。张邦基:宗室词人赵仲御上元扈跸作《瑶台第一层》词,反映了北宋的太平气象。
对乱世之音,宋人多持批判、同情的态度。这以对李后主词的批评为突出。一方面认可南唐君臣尚文雅,小词语奇,一方面言其词作属于“亡国之音哀以思”,含有惋惜、同情之意。由声与政通,必然推出一些词为亡国之谶。宋代词学批评大量材料都是关于词谶的记载。这以自宋初即已开始的对前代的批评为主。在盛世之音、衰亡之音外,声与政通还有一个指向,就是反映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正是“实说”,使词具有反映时代、社会风俗、人情之功用。故宋代的词学批评,大量的内容是词本事的记录和考证,这种实录态度,正反映出宋人词学批评中的社会现实意识。
声与人通:词与作者其人关系的表述
《乐记》在阐述乐由人心感物而发之道理时,往往是可以指向声与人通的。所谓声与人通,在宋代词学批评中,内蕴三层要义:词(声)能真实反映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词与作者为人一致;作者的个性、人格等等内属特征,可以通过词作体现出来。
声与人通,其最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命题,是导出对词作抒发情感——真实情感的认可,对性情的张扬。王灼之所以反对当时先乐后词的填词方式,更深层的原因是:先乐后词,将使词人之志、之情、之心,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实的表达。张耒对词作抒发真情的论述,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其实就是《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的另一种表述;当然,他对情性的张扬,又非《乐记》节情以致中和、中正思想所完全允许。
即使如此,认可情感的真实性,承认小词抒情的合法性,就宋代词学批评而言,还是深具远识闳义的,它必然进一步承认苏轼、辛弃疾等人词作抒发豪迈放达之情的合理合法性。这涉及词与人一致的命题。范开论述了苏轼、辛弃疾两大豪放词代表作家词与人一致的事实,也指出了豪放之情感与词作风格,同样缘乎其人心、人情。
然在词与作者为人一致的问题上,宋人也有疑惑,不是绝对地相信。词与人通,在宋人也多导出词为人谶的判断。其基本思路都是词与人通,词与作者心声、精神状态甚至命运一致。
雅正:对词的整体规范
《乐记》从外物易引致人心之情欲放荡故须以礼节情方面,对乐加以限制。在节制好恶等情欲的基础上,标举“和”、“雅”之帜,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所谓“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先王制乐之方,即在于“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乐记》之论性与情,先天地成为宋代理学思想资源之一,而其“和”、“雅”的标准,亦成为宋人进行词学批评的基石。
综观宋人论雅,内涵三义,一是内容之雅正,特别是对男女之情的约束;二是语辞高雅;三是音律词调高雅。实际上是对词从音律、语辞,到思想内容的整体规范。
内容雅正,是宋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张直夫自觉运用《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于词学批评中,标榜“雅”、“正”。宋末张炎《词源》则进一步正面提出“雅正”、“和雅”、“雅词”、“古雅”、“骚雅”、“淡雅”等概念,且“骚雅”、“雅正”都反复出现,为宋代词论注入新的内容,丰富了雅的内涵。
宋人对俗语、俗词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而又集中在对柳永、康与之等人词的批评上。音律、词调之雅,一是音声之雅正,二是崇尚古曲古谱。
宋人对雅正之崇尚,对郑卫之音之声讨,经由北宋苏轼、周邦彦等人创作上之努力,至南宋词人之明以“雅”命词集,终于形成一场具有一定声势的“雅化运动”。可以说,尚雅的理论与崇雅的创作相表里,相互促进,使宋词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成就一代文学的辉煌。
累如贯珠:五音谐和及歌唱之妙
唐宋时期,词乐犹存,为词而和谐动听,是词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宋人论词歌唱之谐美动听之文字,往往在所多有,而在论述词歌唱之谐美动听时,宋人也以《乐记》为依归。
《乐记》“上如抗,下如坠”等七个妙喻,特别是“贯珠”,早已成为宋人对词之歌唱的最高要求,宋人言及歌唱之美听,自然是“贯珠”;言及贯珠,便自然知道出自《乐记》。仅仅从语言描写角度看,宋人也认为《乐记》之音声描写,达到了中国语言同类描写之最高境界。
要求词合乐美听,讲究“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累如贯珠,一方面使宋词在音乐性上也达到一个顶峰,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宋人走向格律化的创作道路,一以合律、谐婉为归,而忽视、牺牲情感的表达、意境的创造。如此,必使词陷入协律之魔障,而趋向衰落。
《乐记》介入宋代词学批评中,则是经由音乐文学一路,而非诗歌(无论唐诗还是宋诗)、散文一路,更非小说一路,这使《乐记》思想对词学批评的指导,更为直接、剀切。正是这个音乐文学的身份,使宋词较早地接受儒家正统音乐思想的约束和鉴照。故以雅正思想绳衡音乐文体之歌词,远在词之成为独立文体、词体地位得到提升之前,这无疑为宋词的发展扶正了道路,其意义尤为重大。同时,即使像雅正的规范在诗歌、戏曲等文体批评中也必然会存在,但宋代词学批评的雅正论,还包括音律、音调、曲调之高雅;宋人根据《乐记》音乐起源论,探讨词的起源,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使《乐记》指导词学批评的层面更为丰富,内蕴更为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