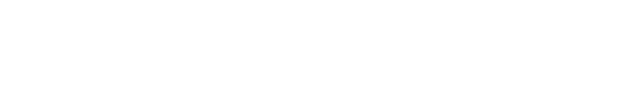9月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中国革命中的性别与女性解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我校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我校当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下,正式召开。来自英国华威大学、利物普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俄勒冈大学以及大陆众多高校的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会议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前五个部分为研究讨论小组,最后一个部分为圆桌总结讨论。
我校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姜进老师致开幕词,介绍了“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的由来,和目前的状况。
会议很快进入第一个主题。由我校历史系的王燕老师主持。王燕还汇报了自己的论文以及英国华威大学姜学豪教授的论文。王燕深入介绍了中文“性”概念缘起。“性”和“性别”概念在清末民初兴起有两大原因:一是日本对原有中文“性”概念的改造。二是西方科学理念,尤其是生物学和解剖学的引进。这一过程发轫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完成。用科学解释“性别”,不仅体现在带有“性”的词汇上,也扩展到了“妇女”、“男子”等词汇。科学界定了两性行为和角色的差异。
接着,王燕老师介绍了Howard Chiang, Mercurial Matter: The Scienc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Sex in Republican China (姜学豪:变化不定:科学和民国时期性概念的转型)一文。姜老师主要从三个认识论维度——观察的对象、欲望的主体、身体的可塑性——探讨并描绘1920年代到1940年代充斥在大众媒体上的多种充满活力的可流动的、可变化的“变性”话语。
接下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余华林老师报告了《论1910-1930年代知识界新式贞操观的演进》。他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贞操问题成为聚讼纷纭的热议话题,在当时报刊上屡屡爆发有关贞操问题的大论战,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包括《新青年》、《妇女杂志》、《生活》周刊上围绕婚姻与贞操、离婚与贞操、新性道德与贞操、恋爱与贞操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通过对这次论战的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当时人们普遍要求打倒旧式的片面的贞操,同时又认为贞操不可彻底废除,主张要建立新式的贞操。新式贞操观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先是将贞操与婚姻相联系,认为贞操就是对配偶保持忠诚;后来将贞操与恋爱相联系,认为离婚无损于贞操,贞操就是对恋人保持专一;最后将贞操的人身依附性完全去除,贞操只与恋爱相关,而且与恋爱互为表里,这种贞操观在二三十年代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在这一组的最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Leon Antonia Rocha做了题为“Teaching Orgasms at two Villages near Tianjin, 1999-2000: Chinese Sexuality and the Ford Foundation”(乐怀璧:天津附近农村的性教育1999-2000:中国的性态和福特基金会)的演讲。他解释了研究的缘起。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天津附近静海的两个村庄里开展了一项普及两性知识的高强度培训计划,对象是当地31位计划生育干部,24名男性和7名女性,以便他们学成后为当地的夫妻提供指导。这项计划的一个成果是一份100页培训指南,题目是《计划生育工作者指南》,其宗旨是一种整体性的良好关系,不仅可以避免与生育有关的病痛,而且使个人在两性关系中得到幸福和满足。这个宗旨于是与中国对于一个管理良好的、有序的两性革命的兴趣相符合,也与加强家庭和睦增进社会稳定的目标相配合。
在这一组的讨论结束后,评论人我校历史系许纪霖老师和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历史系Gail Hershatter(贺萧)教授做了评论。许纪霖老师从历史研究的大处着眼,从概念史和贞操观所反映的历史大背景出发,提出“两性”的出现和贞操观的演进都是源于整套的文化结构制度的改变,而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一些细节的变化。贺萧教授认为,民国时期有关两性的话语非常活跃而且多变,但是我们应当警惕地看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背后的自由主义思维陷阱,不应当全盘加以接受。
会议在短暂的午餐之后,进入新的议题。中南大学的李斌老师做了题为《嵌入农村阶级划分背后的性与性别》的报告。她指出:最初的阶级概念,是一个与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使用情况及其劳动与否紧密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将经济结构和阶级意识及其行动联系在一起,阶级斗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和“历史的直接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早期建设中,更是将阶级划分和革命态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与之相伴随的,是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中国化转变。阶级与性别的叠加,使得正确理解中国的阶级问题绕不开对相关性别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农村父系制、父权制、从夫居的家庭结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以及划分阶级与划清革命界限的相关性,都使得农村妇女的阶级成分主要依父权制家庭的阶级成分而定,妇女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成分。另一方面,为照顾男性贫雇农阶级的情感及其利益,政策又对不同阶级发生婚姻关系产生的划阶级问题作了单独的规定。而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家庭的妇女,则和其家人一起被划入了地主和富农的行列。阶级划分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女性独立和妇女解放并没有被纳入阶级划分的范围。
斯坦福大学的掌门人Matthew Sommer教授的题目为“Discourses of the “Bare Stick”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苏成捷:有清以来“光棍”的叙述)。他追溯了从18世纪到现在有关单身的贫困男性,也就是常被称为“光棍”的那些人的话语。简单来说,他们被妖魔化为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清朝的司法话语中)的替罪羊,到后来在毛时代的农村阶级结构分析中被光荣地称为“革命先锋”。今天,阶级分析法已经不再流行。光棍又再一次被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外国评论人当做替罪羊,用和清代的话语相同的方式,把他们描绘成性的捕猎者,导致了飙升的犯罪率、娼妓业的增长和同性恋的传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清司法话语和当今社会科学和政策话语的惊人相似能告诉我们当今中国的什么问题呢?
这一组的讨论比较简短,但很热烈。我校历史系革命史专家韩钢老师非常肯定李斌的文章,但同时也对她的材料来源表示一定的批评,对于二手研究的使用仍然要注意其真实性。贺萧教授也对苏成捷教授的讨论提出了不要忽略“阶级”的提示。很多学者都提到了正是由于阶级的不同,才导致对人群的区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但也有学者提出,现在的“光棍”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贬义色彩,这也是苏成捷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本次会议的第三组讨论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开始。梁教授多年来一直支持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地推动妇女史在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大力发展。他的报告题目为《中国“性伦文化”研究述评——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实践为例》。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科诸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文学、医学等开始关注并研究“两性”的问题,史学虽然对此相对涉及较晚,但也逐渐了解和关注这一领域,认识到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民生的重要意义。梁教授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实践即学术活动为例,来扼要介绍和评述二十多年来国内有关“性伦文化”的研究状态,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国内性伦文化的研究片段。这也与他从伦理的角度去重新界定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的学术理念相一致。
继梁景和老师之后,山东女子大学社会与法学院的林存秀老师报告了《性别与戏剧表演——民初婚恋问题的历史回眸》。她发现,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戏剧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现代化进程中,戏剧成为正在形成中的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认知,和思想的变迁,往往是在戏剧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获得和发生的,戏剧也最能体现民众心态和社会文化的特点。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精英史观的影响,史学领域对于戏剧研究及其重要性认识不够。林老师以戏剧入史,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通过对民国初年畅演的两部文明戏《双泪碑》和《一缕麻》的微观考察,来展示戏剧和表演在日常生活变迁中的作用,同时兼顾论及男性精英为主导的改良和启蒙运动,给女性带来的真正的解放。
俄勒冈大学历史系教授Bryna Goodman谈到了民国的废妾运动。题目为“Concubines, Quickly Awaken!” Visions of Eq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Republican Era(顾德曼:“为人妾的女子们快快觉悟罢!”:废妾运动与民国时期平等与性别的理解)。顾教授主要关注新民国新文化运动时代公共话语中对于妾的讨论。与公共话语中先锋派“新女性”的崛起相伴随的是对于妾这个被鄙视的形象的新关注。妾不仅对于民国创造新女性还是更广义的创造新公民崇高事业来说,都是“人类进步的障碍”,相悖于民国以个人人格、自立、自由恋爱为基础的政治理想。本文以当时报刊杂志上、诗歌小说中、女权主义宣言中关于妾的描写为资料,追寻关于妾的形象之建构的一些关键轨迹。当时反妾运动的特点是旨在消灭传统家庭制度的残余。顾教授总结说,如果说新家庭是民国新政体的象征,那么,妾就是民国的毒瘤。这也是民国废妾运动背后的逻辑。
最后我校历史系博士生王瀛培报告了《性与性别的医学检验:建国初期上海婚前健康检查的短暂试行》。王瀛培选取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新中国的婚检规定来探讨新中国对医学、婚姻、家庭、健康的理解。王瀛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颁布了新《婚姻法》,其第五条对欲结婚之男女双方的身体健康做出了明文要求。为了践行此条文,全国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婚前健康检查,上海便是其中一座。上海试行婚检过程中,男女双方的生理问题变得瞩目,“器官缺陷”与“性病”广为聚焦。当然,新《婚姻法》背景下的婚检中也必然与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别”问题密不可分,其中既体现在医学对婚检的学术表述中,又反映在婚检在两性身体的具体实践中。前者显现了身体性别的平等,后者则出现了偏差,最终反映了社会性别的差异。此次婚检仓促结束,虽然有客观条件上的原因,如医疗资源的缺乏,但社会性别问题还是其主要内因:卫生部门对之平等追求的无力承受。另外,这些问题背后,或许还牵涉到逐渐开始被批判的优生问题。建国初期上海这次婚检的试行,既是对两性身体的检验,更是对共和国初期社会性别问题的一次医学检验。
这组讨论的最后,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陈雁教授做的汇报——《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陈教授非常独特地关注到了中共一大背后被遗忘的那些女性。她指出,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游鑑明教授希望梁景和老师的实践能够再发扬光大。游老师也提醒林存秀老师在探讨不同的历史文本时,一定要注意历史文本的再现问题,它背后所隐含的话语。另外,游老师也指出,民国时期有关废妾运动,不仅要放在中国的背景下来看,还要看到它是一个全球的思潮所引导的。最后,游老师总结道,她评论的三篇文章其实有一定的共性:有人从媒体部分探讨那个时候的婚恋问题,有人从戏曲方面做它,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个戏曲还可以加到其他的戏曲、小说、或者是言论的比较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精深。许纪霖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瀛培论文中缺乏的对大历史的关怀,婚检这个表面现象其实蕴含着中国人在新中国对于婚姻、家庭的全面理解。许纪霖老师还特别谈到了陈雁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和两性问题在历史中的特殊性,以及所反映的人性的幽暗面。
会议进入第二天的议程后,第一场的讨论以兰州民族中学教师王昭《自我异化的起点:范元甄在延安的日记、书信解读(1940-1945)》为开场。王昭介绍了文章的缘起: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刊载了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后有“好事之徒”放到网上,一时间议论纷纷。1999年,湖南《书屋》将该文在内地发表,引发国内多家报刊竞相转载,伴随诸多非议。李南央所解读的母亲范元甄,一辈子除了扮演好了一个对党国忠心不二的“老革命”角色之外,作为亲人,无论哪种角色——妻子、母亲、姐姐,范都极其失败。在李南央以及众多对“这样一个母亲”的讨论者笔下,几乎都认为范元甄的延安经历,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李锐被抢救后,范元甄受到牵连,以致此后生发的种种事端,是范自我异化的一个起点。延安的斗争经验成为范元甄日后处理此类事件的一个经验样本。延安前后,范元甄经历了结婚、生子、被抢救、离婚、复婚等许多人生重要的时刻。前前后后,范元甄在认知和行为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幽微的转变过程。延安整风运动是李锐与范元甄二人走向殊途的起点,范元甄在此异化,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在建国后政治运动中的性格暴戾与行为乖张。王昭认为,除却个人因素,由范元甄的“异化”可透视出革命女性的一些共性问题。赴延安之前,李锐与范元甄之间所培育的“同志之爱”,就埋下了夫妻间党性第一的伏笔。初到延安至整风之前,范元甄身为革命女性面临回到家庭的两重困境:在显性层面,对生理现象的无知、几乎没有避孕措施、周末夫妻制等,使得范元甄等革命女性稀里糊涂怀孕,难以平衡生养与流产之间的困境;在隐性层面,延安的性别平等定义模糊,与传统断裂、看似解放了的革命女性承担了比往日更多的责任,在处理家庭与事业问题和日常琐事时颇感两难。整风之后,党内开启自我批判的大门。女性承载着更多“落后”的非议,因此对“进步”的要求更为急切。随着丈夫李锐的被“抢救”,范元甄在自我与集体的压力之下,对李锐由信到疑,继而与“旧我”全面告别,走向“新我”。
姜进教授接着王昭的话题,继续讨论了“国族话语中的性与性别”。姜进教授追问:“性别”能不能进入史学领域?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者可能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行为能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中国传统史学对此是回避的,而且视之为禁忌。那么,没有“性别”的历史难道真的能算作是人类的历史吗?这是一个合理合法的问题。但是,更加艰难的问题可能是:如何能够让“性别”进入史学,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合法领域。自从福柯发表了他的三卷本《性史》,女性主义和新文化史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有兴趣,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福柯的《性史》算不算历史学?尽管史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也有史学家不予承认,但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里,与性有关的议题近年来逐渐出现,从贺萧有关上海妓女的研究、韩起澜有关文革中女知青的研究,到吕芳上关于“爱情加革命”的论文到李海燕的“爱情”系谱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在此基础上,姜进将视线投向战时上海,聚焦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中的性别与性态,考察性别与个人、民族、政治认同之间的动态张力。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Zhao Ma教授作为这一小组的第三位发言者,讨论的题目是“Writing the Unspeakable: Soldiers, Sex,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bout the Korean War in 1950s China”(马钊:书写无言者:战士、性和大众文学中的朝鲜战争)。马钊探索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书写和大众记忆中的重要地位,战争中确立的“中朝同盟”不仅是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基础,也成为冷战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马钊发现,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活动,朝鲜题材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朝鲜女性形象。她们被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是敌人杀戮、强奸、劫掠的对象。被损伤、凌辱和扭曲的妇女的身体,成为战争暴力的见证。文学作品中还大量描写了母亲失去儿子、儿童失去父亲的场景,妇女经受家庭破碎的痛苦,承载战火摧毁家园的创伤。“女性化”(feminized)的朝鲜形象反衬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邪恶,更加凸显中朝同盟的必要性与正义性。通过虚构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语境中经典的“军民鱼水情”的叙事模式延伸到了异国他乡,用大众所熟悉的家庭话语诠释了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诠释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志愿军战士以兄长、儿子、父亲的身份融入异国战地生活,完成革命话语下中国对同盟国的扶危济困与政治启蒙的光荣责任。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的朝鲜叙事影响深远,不仅强化了中朝两国友谊与军事同盟的战争宣传主题,也建构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想象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输出革命的大众文化基础。
我校原党委书记,现思勉研究院研究员张济顺教授给出了一段私家历史《革命女人的性爱困境:李明的故事》。张济顺教授谈到她自己对于革命妇女的理解,和革命与日常生活的纠结。她想让这些有着各种光环的非凡女人走进历史的“平凡世界”,让人们知道,无论是怎样的“革命”,她们也不能逃脱无数的人生“日常”: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悲欢离合。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革命与性别之类的日常问题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她们的日常故事可以发生在无数非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女人身上,也包括她们自己——一夜之间,由“革命”变成“反革命”。但正因为是革命女人,尤其是革命的“名女人”,她们的“日常”也成了“非常”,或被赋予“崇高”、“神圣”,或被斥为“冷酷”、“变态”,或被抱以“怜悯”、“叹息”,不足云云。总之,当革命走进她们“日常”的时候,她们就身不由已了:当革命书写成为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她们的日常完全被遮蔽了;当革命被“告别”的时候,她们又被遗忘了。而当革命史被冠以“新”字要重新阐释,重新书写的时候,她们似应回归了。不过,这一次的回归,应当把她们置于真实而平凡的史学世界里,拾回本该属于她们的日常,那个为革命所浸润、所瓦解的日常。让她们属于连接着大历史的无数生命个体的一部分,普通人的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革命女人们的人生日常也将如一部部“乏味的,没有故事性的小说”,但“绝不是某个人的历史底回声”。
本组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赵婧女士。她的题目为《抗战时期的妇女医疗救护——以战争动员为中心》。她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动员全民族参与抗日战争的声浪中,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有责任积极投入抗战工作。医疗救护被认为是战争中最适合女性从事的事业之一,为解决战时救护人力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和妇女团体纷纷动员与组织女学生、女职员以及家庭主妇等参加救护训练班,女护士、女医生等专业医疗人员更是国民政府征调至前线或伤兵医院服务的对象。因此,赵婧试图分析动员女性从事医疗救护的话语建构,梳理妇女医疗救护的基本构想与实践,从一个侧面呈现战争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对于这一组的讨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同时评论人及各位学者也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意见。针对王昭,学者们质疑,像范元甄这样特殊的女性,可以用常人的方式去理解她吗?尤其是杨奎松老师提出,范元甄这样的女性,也许更需要从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度剖析。刘昶老师提出,姜进老师的提问没有太大意义,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苏成捷教授指出,纪律和爱国主义以及情感其实有一定的不兼容性。日本国立德岛大学教授邵迎建建议,赵婧的材料不仅仅应当从国家动员的角度去找,也应当从妇女本身去找。
会议的最后一场讨论从我校历史系著名党史专家杨奎松老师开始。杨老师的题目很有新意,为《“流氓”“坏分子”——一名干部培养对象被发现的“犯罪”经过》。这是一篇纯粹从档案资料中来的文章。臧其仁,出身贫苦,新中国建国后从团员做到团支书,从普通工人做到以工代干,并成为厂中颇有影响的工会副主席,还代表厂工会出席过市代会。臧其仁开始走背字,和1958年厂里开始整风有关。对臧解放前历史问题的调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怀疑,这些调查最终并没有能够发现臧其仁任何值得上纲上线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却意外地查出他的一系列“流氓”行为——多年来与多位同性发生性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臧的这种性倾向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灾难性后果。他先是被定性为“坏分子”,文革结束后还被作为流氓犯罪分子处刑七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Zheng Wang教授接着作了发言,题为“From Xianglin’s Wife to the Iron Girls: the politics of gender representation”(王政:从祥林嫂到铁姑娘:性别再现的政治)。王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见证了性别话语和实践的剧烈变迁。对性别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的争论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权力争斗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伴随着阶级重组和意识形态之争。人们的生活已经被深深地卷入这场产生冲突、矛盾的性别规范和规则的权力领域,其普遍性却对我们的分析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篇文章主要关注性别再现的政治,缩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性别化的权力斗争的范围,同时为过去六十年中的历史断裂提供一个连贯的历史叙事。王政选择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两个著名的性别话语的象征——祥林嫂和铁姑娘,来追溯这些性别化的符号被生产出来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使它们的涵义发生争论、被改变的不同政治背景。通过考察祥林嫂艺术形象——这一最初在1920年代新文化语境下被描绘成“封建压迫”牺牲者的经典形象——的不同形式,并找出那些具体的文化生产者,分析他们的目的,王政在五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之间找到了某种有形的联系。中国有关共和国的学术很少注意到五四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反映了一种简化主义的倾向,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性别偏见。王政把祥林嫂这个共和国时期家喻户晓的名字纳入研究,以此来考察共和国早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转型中的性别政治,并从性别的角度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时期。如果说祥林嫂的象征意义变化不大,铁姑娘的涵义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给我们搜寻共和国的历史断裂提供了丰富的契机。铁姑娘不是假想的形象,而是活生生的年轻女性。她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农业或重工业领域从事超强体力的工作。这个名字最早指称一个模范集体农村——大寨——的一组年轻姑娘。铁姑娘队受国家表彰,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被全国效仿,1976年文革结束后却遭到批评。表彰或者妖魔化铁姑娘代表了文革前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描绘不同的铁姑娘形象背后那复杂的斗争,使王政得以探讨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主导性话语是如何生产的。在中国共产党决定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后,很快出现了精英阶层对这些社会主义劳动阶级女性形象的谴责,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受过教育的精英和国家合作,阶级和性别权力关系开始改变。最后,通过性别和阶级的视角可见,祥林嫂和铁姑娘文化形象的建构和解构说明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知识生产的政治。
紧接着,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Emily Honig和圣芭芭拉大学的Xiaojian Zhao教授作了“Sent-down Youth,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韩起澜、赵晓建:不当的亲密关系:文革中的下乡知青与性侵犯)的报告。两位报告人发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学术文章和大众文艺作品中,下乡女知青在地方上所遭受的性侵犯及女性作为受害者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总是穿插了城市女性在乡村被村干部和农民强奸的情节。两位研究者在江西、黑龙江和云南等地的档案馆搜集了大量有关知情遭性侵犯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两位试图超越简单情节剧式的描述而追究现象背后的问题。她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1970年代初期的一批有关性侵下乡知青的调查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那么,中央在多大程度上对此进行了干预并制定下达有关政策规定的。她们注意到中央规定中对性侵概念的定义包括了强迫的或欺骗性婚姻。她们还考察关于强奸的考量是如何处理下乡女知青以提供性服务来换取回城机会等特属待遇这样的问题的。她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性侵犯如何反映了文革时期的城乡关系。女知青在乡下缺乏家庭纽带的保护,她们写给城里亲人的求救信,城里家长向有关部门的反映情况请求解决的信件,都是她们研究的素材。城里政府派去的慰问团所撰写的材料也反映了城里人将农村视为混乱之地的看法。两位报告人指出,她们的研究并不是要补充关于下乡知青遭性侵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些案例来观察文革时期的城乡关系。
两天会议的最后是中国传媒大学王宇英老师的报告《从弃父到失真:“文革”时期家庭革命的罪与罚》。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一度遭受猛烈冲击,特别是许多黑五类家庭,不仅要承受来自外部社会的巨大压力,内部也发生了分崩离析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对于去性别化及革命化的政治宣传都曾持积极认同的态度并努力践行,对“反革命“或“不革命”的家庭成员积极造反,对“落后”家庭常常采取离弃、批判的态度。这种激烈的“弃父”现象,来源于“五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积淀,与青春、理想、信仰、追求、利益等共同交织在一起,最终演成了特殊年代中的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革命伦理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与对立,令许多女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承受价值观撕裂带来的压力和痛苦,昭示着那个时代无可辩驳的荒谬与尴尬,也预示着其最终走向失败的必然结局。“文革”大潮跌落之后,革命话语崩溃,真相消解,女性价值和角色的进一步错位。
这场讨论是整个会议期间最为热烈的一次讨论。围绕着杨奎松老师的研究,我校历史系教授冯筱才指出,杨老师把工厂内迁和臧其仁的问题放在一起看,很有见地。但学者们也质疑,臧其仁的问题不该由他自己负责吗?李南央老师针对王政的文章,看到有关中国妇女性别再现的不稳定性,提出要有中西不同国家的比较,而不能只能中国的内部纵向比较。应当从法制的角度,稳扎稳打,把妇女的权益通过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冯筱才老师非常肯定韩起澜和赵晓建的档案搜集工作和城乡关系的探索。但李南央老师批评韩起澜和赵晓建没有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法制缺失给中国城乡带来的问题。最后对于王宇英老师的论文,冯筱才老师一针见血地提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太过明显,而且并没有在文中清晰地展现性别问题。
在会议最后的圆桌总结上,大家热烈讨论了社会性别和女权主义为什么在大陆被边缘化的原因。还讨论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理论先行,还是事实先行的问题。究竟应该先从理论的角度去阐释历史,还是从历史来发展理论。在座的学者都倾向于后者。贺萧教授从两天发言的论文中总结出了一些紧张的关系,认为历史发展中性别和阶级、革命等都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同时,她也指出,我们提出“解放”的概念,还是有其道理,我们还要对“解放”抱有热烈的希望,才能给我们自己更多的解放可能。